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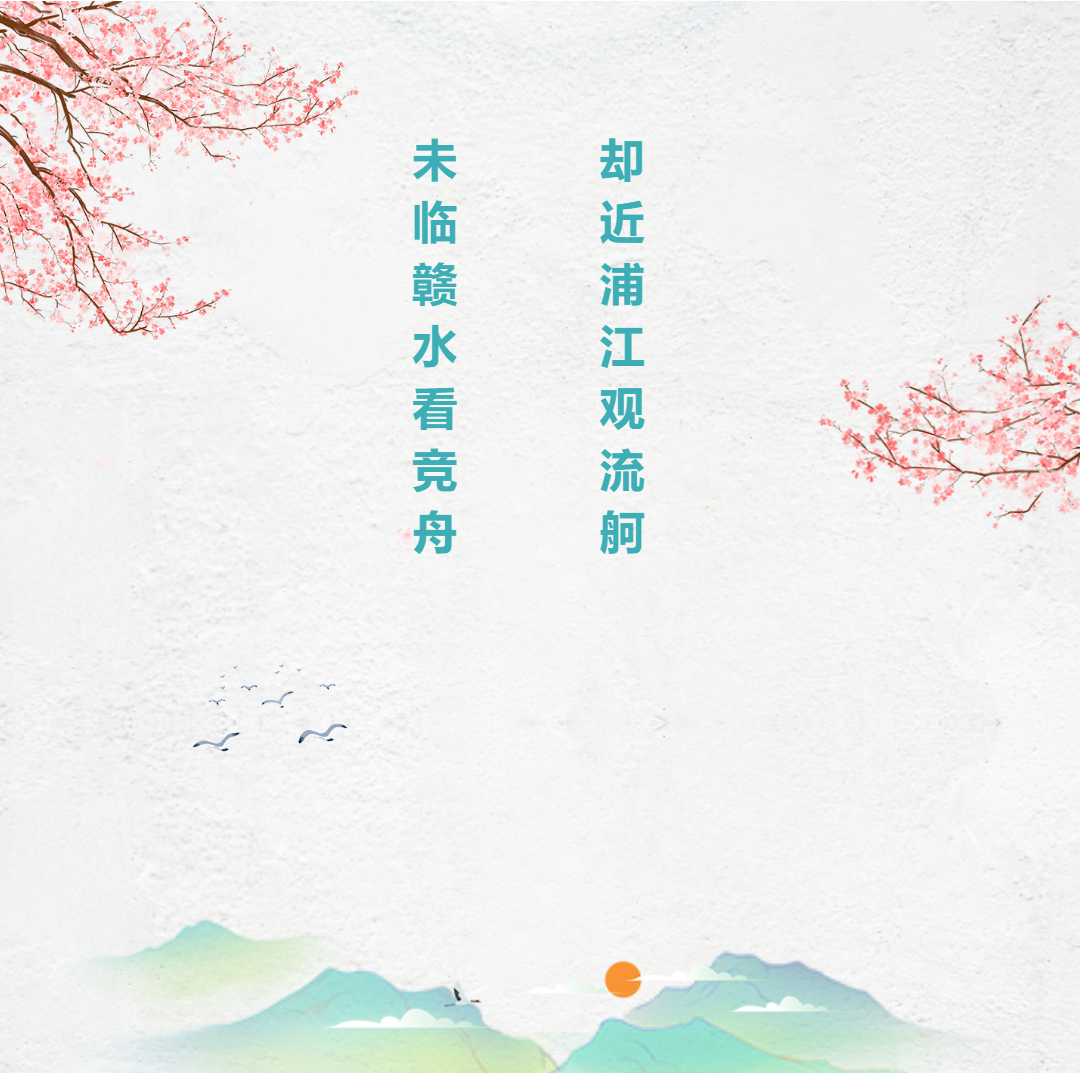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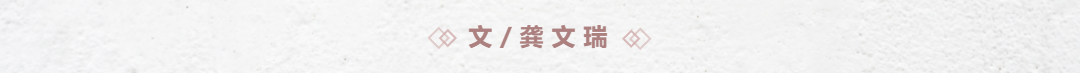
所有的生命都与水有关,生命的所有行走都与河流有关。人类最早的雏体是从海洋走向陆地的,族群的一次次迁徙都是选择水岸重构家园的。顺着河流行走,每一个人都可以彼此相遇。纵横交错的江河湖海,则把我们行走过的每一个驻足地的信息都互相流通。

今年端阳,家人们从中国的各个城市来到沪上,相聚在黄浦江边。聚餐的酒店在一幢高楼的25层,两面望江,风月无边,城市不尽的楼宇、街道与人群,尽然匍匐在脚下。流动的风景是俯视中穿城而过、蜿蜒迤逦的黄浦江。身居高处,江水的流动是看不见的,但浦江上川流不息、往来穿梭船舶,让黄浦江生动了起来。一霎那,令人有一种仿佛触摸到到了这座都市的大动脉在澎湃流湍的感觉。一江大舸竞流,两岸高楼耸秀。此情此景,令我很自然地联想起微信里不断涌来的家乡赣州端午节龙舟竞渡的情景。
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又是驭龙逐浪时。通过一祯祯照片和一则则视频,我宛然置身于端午节的赣州章江岸畔。但见四十余支龙舟轰然下水,一支支龙舟劈波斩浪,奋楫争先,一场场速度与激情的水上盛宴就此铺开。

疫情三年,江河安静了三载。虎平兄告诉我,人们积蓄了太多太多的情愫。是呵,对江河的敬畏,对山水的向往,对屈原的崇拜,对生活的热爱,对疫情的怨弃……这一切如同将欲喷发的活火山,人们企图寻找一个释放的关口,在某一时间某一空间一次性腾空内心累积的那份沉甸甸的负重。终于,初夏微薰的软风中,五月初五的端午节迎合了人们的这份长情和冀望。
龙舟竞渡,形成于汉魏。吴国人周处《风土记》最早记录了端午竞渡,说明三国时“端午竞渡”已成为风气,当然,那时祭龙神的成份多些。龙舟竞渡附丽为纪念屈原的内容,唐代魏征在《隋书·志》中留下了佐证,有曰:“屈原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上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齐驱,梢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率然。”自此,端午竞渡这一民俗统一在了纪念屈原这个具有凝聚力的主题上。

岁月流转,龙舟竞渡已由一种纯粹的民俗事项,在近几十年来演绎成了一项竞技运动。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项鼓舞人心的运动。打记事起,我看过近十场龙舟赛。印象中,每次观看龙舟赛,我都会为之沉醉。一方面,为驭手那种远远超乎平寻常的力量的迸发,以及不能自抑的激情的放纵而沉醉,另一方面,也为观众那种不由自主的追望与呐喊而沉醉。那是怎样动人的情景呵!一一龙舟一路传来的棹声鼓声号子声,与岸上沿途观者不断发出的欢声笑声呐喊声,遥相呼应,绵绵不绝。平阔的水路,飞驰的龙舟,逶迤的江岸,喝彩的人群,美美与共,天人合一,衍生出一道何等美丽的风景线,演绎成一幅宛若清明的上河图。
此时,天空的宁静早也碎了,往日成阵的鹭鸟也失了踪影。天穹以其无形的眼眸俯瞰着大地,惊喜这个日子里的人类,性情怎么会如此的解放,惊喜河流之上那一支支如箭一般穿行的龙舟,那刚刚点晴过的龙头呲牙咧嘴竟是如此的笑靥如花。看到了吗?那些驭龙逐浪的汉子们,身子被江水浇了个透彻,身体中那胀鼓鼓的肌肉将力量整齐划一地传递到了棹桨上,一呼一吸间,驭驶的龙舟被驱动得疯一般地狂飞。

显然,龙舟竞渡这一民俗是独具魅力的。从人文的角度来诠释,我会将之理解成是一次文化与精神的大场景下的大阐发。古人智慧而多情,他们选择了以屈原的忌日为节日,从此中华民族的文脉里就浸洇了一种淡淡的忧思,以及绵绵的诗意。每次龙舟竞渡,我都会思接遥远。我遐想,端午龙舟竞渡的喧嚣,可有把人们祈求风调雨顺的愿望传递到位,主宰一方水域的龙神应该颌首应诺了吧?可有把江水里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屈子的魂灵唤醒?那无数的桨棹激起的浪花可有屈子的楚辞在其中点点流淌?若果真如此,被中国人赞之忠肝义胆、满腹才情,敢于以身殉国、以身殉道、以身殉志的伟大屈子,在天国亦当含笑了。其实,快乐地互祝“端午安康”的每一个国人都应该欣慰,能生活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国度一一文化如此缤纷绚烂,文明如此源远流长。
源远流长、上善若水……中国的诸多成语都与水有关。水与文化或文明是有紧密关系的。水脉即文脉!记得那天我写下这几个文字时,甚至有些小喜悦。是呵,水流向哪里,文化便滋润到哪里,文明便在哪里放光。比如,北方人爱吃水饺,顺着河流迁徙的汉先民则把这个习俗带到了南方,南方种不了麦,便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地创造出了“酿豆腐”这道被孙中山名之“怀乡念祖菜”的客家美食。或溯水,或顺流,或溪河,或江海,因纪念投汩罗江的屈原而衍生的端午节,以及因节气而衍生的包粽子、划龙舟、插艾草、佩香囊、洗暖水澡(艾草、昌蒲煮水)、喝雄黄酒……等端午民俗,也从楚地被传播至吴越,最终泛衍到了华夏大地。

地处吴越的上海人,自然也过端午节。某些习俗甚至还更显创造性,比如喝雄黄酒的习俗被植入进了越剧《白蛇传》,比如嘉兴的粽子做成了产业化。古老的苏州河上也一直都有龙舟竞渡活动,只是黄浦江上的龙舟竞渡见得少了,以致许多上海老人还一直念叨着1948年黄浦江上的那场端午龙舟赛。十里外滩人头济济,万人争看浦江竞渡,弄堂人家门上挂艾,男孩女孩菖蒲作剑......那天的《新民晚报》载曰:“今日为端阳佳节,本市市民所深感兴趣之龙舟竞渡,今晨在黄浦江中热烈举行。参加龙船计11艘,分成红、白、黄等各色。清晨七时许即纷纷在浦东周家嘴码头集合。正九时出发北行,各船上金鼓齐鸣,香烟缭绕,爆竹声此起彼落。舟入市区沿江时,岸上观者如堵,各码头并备香案,于龙舟划近时,纷纷燃放爆竹。沿途经南码头、董家渡、张家宅、老白渡、杨家渡、新开河、洋泾浜等各码头。正午12时,舟抵外滩公园,时公园中万头攒动,人山人海,若干人并高踞大树上瞭望。”街头有卖香袋粽角者,五颜六色,甚为精致。中药铺雄黄生意大佳,价涨一二倍。戏院十之八九上演“白蛇传”。路上到处有鲜鱼、肥鸡、枇杷、粽子……
龙舟竞渡之外,端午的节趣潜入民间,分散到了各家各户。比如,家家户户挂艾草、吃粽子。每年端午节前,儿子一定会买回来一大堆嘉兴粽子,我一定会去菜场买上几支艾草插在大门上,以应节气。今年端午节还有两件小趣事,节前一日,疫情期间建立的一个团购群的群主发来的微信:“祝端午安康,粽横四海,粽是走运,粽是快乐 。”粽子的芳香穿透屏幕,扑面而来。今天聚餐上电梯前,我带着三岁不到的大孙子在大堂玩耍时,还见到一对穿汉服的小姐妹,两人各自的腰带上系着一只绣花的香囊,那香草的味道好闻极了,把孙子诱惑得直往前凑。

浦江之东,上海最繁华最现代的区域。三十多年前,刚刚开发开放的浦东还飘逸着田野蒿草味,来自四面八方的建设者汇聚于此,新兴的城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长着。其实,城市无论怎样扩张,厚植于这片土地里的人文底蕴不会改变。鳞次栉比的高楼下,仍有传统乡事在发生,仍有民间习俗在演绎。在航头镇,十年前从江西迁居过来的树才兄,自诩为新航头人。他的眼中,田间艾草处处茂盛,水边菖蒲丛丛青绿,航头的乡景并无别样。他在文章中记述了航头人的端午节庆活动一一家家大门上悬挂着菖蒲、艾叶、蒜头,亲家告之:吾伲以菖蒲作宝剑,以艾作鞭子,以蒜头作锤子,有了这〝三种武器”,可以驱除蛇、虫、病菌,斩除妖魔。航头人聪明,用芦苇代替棕叶,因为航头下沙一带,水源充足,芦苇茂盛,芦苇叶唾手可得,包粽子不愁粽箬。亲家们集中在祠堂里包裹糯米的芦苇叶,就是村里亲家在野外采来的。“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这儿端阳,那儿端阳,处处是端阳”。新上海人的笔下,上海端午的节气浓郁如斯,似乎一点也不比湘鄂赣这些楚国故地差。
未临赣水看竞舟,却近浦江观流舸。与故乡章江或苏州河百舸争流的龙舟赛比较,我更喜欢些黄浦江船来舶往的情景。我以为,前者更多的是应节气之景,是一种竞赛兼表演性质的节庆仪式,体现的是鼓舞人心的精神作用,本质上属于一种民俗趣味的文化现象。而黄浦江川流不息的船来舶往之情景,则是一种朴实、写真的物流姿态,完全可以比喻成是中国经济活跃与否的动态图。

自2018年定居上海后,我曾无数次走近黄浦江,东西两岸的所有滨江步道我都徜徉过。春暖花开时,我在青浦探过浦江源头淀山湖;夏季清晨里,我在十六铺码头听过钟声悠然响起;秋日黄昏中,我在陆家嘴看过江水潮起潮落;冬天暖阳下,我在吴淞口透过芦苇丛遥望过浦江与长江汇流处的茫茫天际。不过,最让我眷顾的并不是这些为人们早已熟稔了的景致,而是黄浦江上那总也看不够、数不过的穿梭不止的船舶,那些大小不一的游览船、邮轮、游艇、客渡船(渡轮)、杂货船、散货船、水泥槽罐船、拖船、救助船、公务船、趸船、帆船、工程船、测量船、消防船……它们或横渡东西,或近域作业,或由吴淞口逆水而入沪上,或自浦江东流而进江海,来来回回,往往复复,点綴着一江旖旎,流动着魔都风情,演绎着城市故事。
诚然,黄浦江作为上海的母亲河,除了提升城市沿岸景观之外,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其巨大的航运价值一一黄浦江的货运量在国内仅次于长江、珠江、京杭大运河,排名全国第四,是一条世界前十名的“黄金水道”。大舸东流,奔腾入海。黄浦江航道从长江口至松浦大桥一段可通万吨巨轮,松浦大桥至毛竹港可通千吨级轮船。上海市60%以上输入货物和98%以上外贸物资均由此航道出入,安徽,江苏,浙江,长江流域,甚至国内沿海城市的货轮均可以通过黄浦江货运直达上海市腹地。年货运量约两亿吨左右,实际价值相当于四条铁路。

大江东去,浪淘沙。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浦东有了一种由里至外的伟岸与令人敬畏的厚重感。不仅高楼如林、流光溢彩,而且创造力勃发、软实力雄厚。如同一台高速运转的引擎,浦东正引领着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经济一路腾飞,也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富有海派风格的人文景象。不夸张地说,完全可以把富有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之城市精神的上海,比喻成中国经济腾飞的龙头。疫情肆虐的三年,阴霾笼罩着上海,上海不得不暂时低下她高贵的头颅,按下经济发展的暂停键。直到今年梅花盛开时,疫情远去,上海复归繁华,南京路的人流重新熙熙攘攘,鲁迅公园的歌声再度响彻天空,黄浦江上又见大舸穿梭往来。一切都在好起来!我期待,经过磨难的大上海,经济引擎的马力开的十足,浦江之上重现千舟竞发、大舸东流入海去之泱泱气象,为中国社会经济全面复苏赋予强劲的推动力。伫立黄浦江咩,我作如是想。
是的,一切精神的或仪式的事项,最终当转化成物质的或力量的显现。如果说故乡或苏州河的龙舟竞赛彰显的是一个地域的精神力量与文化软实力,那么从黄浦江出发抵达五湖四海的大舸大船,航行在世界各大洋的中国远洋货轮,就是一艘艘巨大的龙舟,它满载着上海人民的深情厚谊,以及中国人民的美好希冀,与世界各国的货轮一道,破浪前行,正呈现着另一种形式的泱泱大气象之竞渡。
2023.6.25于浦东

龚文瑞,笔名文瑞、谷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中国明史学会王阳明研究会副会长,江西省地域文化研究会专家顾问,赣州市政府古城保护委员会专家顾问,赣南师大文学院特聘教授。赣州本土文化研究著名学者,著有《客家文化》《客家故园》《赣州古城地名史话》《山水赣州》《苏轼与赣州》《王阳明南赣史话》《赣南书院研究》等近三十部专著。
—END—
编辑:叶焱文
审核:李 欣

※ 特别声明:本公众号仅用于赣州市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及群众文化艺术普及,不用于任何商业用途。所转载文章及图片、视频、音频等版权均属原作者。如有侵权,请及时与本公众号联系。



 版权所有@2020 江西省赣州市文化馆
版权所有@2020 江西省赣州市文化馆
 备案号:赣ICP备20006421号-1 备案查询
备案号:赣ICP备20006421号-1 备案查询